既不科学,也无幻想:为何《爱死机》的“宠物之爱”让人失望
既不科学,也无幻想:为何《爱死机》的“宠物之爱”让人失望
既不科学,也无幻想:为何《爱死机》的“宠物之爱”让人失望备受万众期待的(de)网飞科幻神剧《爱、死亡与机器人》第四季(dìsìjì)近日上线流媒体平台。然而,与第一季斩获9.2分超高评分的命运不同,第四季一上线便遭遇了滑铁卢,目前豆瓣评分仅为4.8分。其实,这一季《爱死机(sǐjī)》下了大力气讨好观众:剧组趁着宠物经济的东风,特意制作了许多和(hé)可爱动物相关的内容,比如(bǐrú)第三集中女主为了外星(wàixīng)异宠甘愿(gānyuàn)放弃生命,第五集猫猫策反机器人统治世界,第六集海豚(hǎitún)重生成为外星神,第七集霸王龙的复仇,还有第十集的猫咪大战撒旦。剧组急不可耐地为观众奉上当代最广为流通的伴侣动物作为情绪代币,但显然观众并不买账,萌宠(méngchǒng)无力拯救第四季的风评。
 《爱、死亡与机器人》第四季剧照,猫咪大战撒旦拯救(zhěngjiù)世界。
在笔者(bǐzhě)看来,剧组费心缴纳的“萌宠税”其实正巧(zhèngqiǎo)揭示了第四季失败的原因——第四季完全失去了其科幻内核和对“何以为人”问题的思考,成为了一部充斥着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的萌宠刻奇大展。
一、被改编(gǎibiān)的萌宠叙事:作为“普世”情感的宠物之爱?
本季第三集《蜘蛛玫瑰》改编自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同名短篇小说。主角(zhǔjué)“蜘蛛玫瑰”(Spider Rose)是一名经历了机械化改造的赛博格人,她(tā)独居于宇宙边缘的空间站,心中充满了仇恨和孤独,一心想为死(sǐ)于屠杀的丈夫复仇(fùchóu)。
某日,一群名为“投资人”(Investors)的外星种族来找女主做(zuò)复仇所用的技术/武器交易谈判。临别时,它们将一只名为“小鼻子”(Nosey)的小型(xiǎoxíng)异形生物托付给蜘蛛玫瑰照顾,以作为谈判期间的“临时交换品”。随着时间推移,小鼻子逐渐填补了蜘蛛玫瑰生活中的情感空白,女主角(nǚzhǔjué)时不时爱抚(àifǔ)它,小鼻子也在她遭遇(zāoyù)仇人的袭击时出手相助,二者建立起了人宠(chǒng)之间的深厚羁绊。
《爱、死亡与机器人》第四季剧照,猫咪大战撒旦拯救(zhěngjiù)世界。
在笔者(bǐzhě)看来,剧组费心缴纳的“萌宠税”其实正巧(zhèngqiǎo)揭示了第四季失败的原因——第四季完全失去了其科幻内核和对“何以为人”问题的思考,成为了一部充斥着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的萌宠刻奇大展。
一、被改编(gǎibiān)的萌宠叙事:作为“普世”情感的宠物之爱?
本季第三集《蜘蛛玫瑰》改编自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同名短篇小说。主角(zhǔjué)“蜘蛛玫瑰”(Spider Rose)是一名经历了机械化改造的赛博格人,她(tā)独居于宇宙边缘的空间站,心中充满了仇恨和孤独,一心想为死(sǐ)于屠杀的丈夫复仇(fùchóu)。
某日,一群名为“投资人”(Investors)的外星种族来找女主做(zuò)复仇所用的技术/武器交易谈判。临别时,它们将一只名为“小鼻子”(Nosey)的小型(xiǎoxíng)异形生物托付给蜘蛛玫瑰照顾,以作为谈判期间的“临时交换品”。随着时间推移,小鼻子逐渐填补了蜘蛛玫瑰生活中的情感空白,女主角(nǚzhǔjué)时不时爱抚(àifǔ)它,小鼻子也在她遭遇(zāoyù)仇人的袭击时出手相助,二者建立起了人宠(chǒng)之间的深厚羁绊。
 《蜘蛛玫瑰》中女主角与(yǔ)“小鼻子”(Nosey)。
联手杀死(shāsǐ)仇人后,本以为幸福就在此刻降临,然而故事(gùshì)的方向(fāngxiàng)却残忍地一转——与仇人的恶斗毁坏了空间站,蜘蛛玫瑰与小鼻子(bízi)被困太空,补给告罄,最终,小鼻子由于饥饿,欲将她吞噬。而她,在忍受了丈夫死后漫长的孤寂后,再次感受到宠物之爱(zhīài),竟也允许自己被宠物吞噬。
导演 Jennifer Yuh Nelson在采访中透露,这一“牺牲自我、成就宠物(chǒngwù)”结局其实是她做出的(de)独立改编。与剧版结局不同,在布鲁斯·斯特林的小说中,是女主角吃掉了宠物,而非反之。Netflix赞同这一改编的商业决策是出于维护(wéihù)付费者情绪(qíngxù)的目的,避免让观众看到一只可爱的动物(dòngwù)(尽管是虚构(xūgòu)外星动物)遭受伤害。因为现实中,尽管观众对(duì)人类之间相互的暴力早已麻木,却仍对拟人化、娇小蠢萌的动物保留着极强的同情机制。
这段改编恰恰展现了(le)本季《爱死机》的(de)薄弱环节:它表面上尊重动物、远离了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的藩篱,但实际上又(yòu)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延续与加固。它堆砌了一段看似感人至深的情绪(qíngxù),实际却经不起任何仔细的推敲——它假设“宠物之爱”是天然而恒久的,却忽视了“人-宠”关系本身是特定的生物基础、历史性与社会结构的产物。
二、当碳基身体和社会结构都被改造(gǎizào)后,人还需要宠物吗?
《蜘蛛玫瑰(méiguī)》的小鼻子在女主身边经历了一次变身,从类似于水熊虫的可怖模样(múyàng)变成了毛茸茸、大眼睛的类哺乳动物。而女主也热衷于抚摸这个(zhègè)毛孩子,从爱抚宠物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慰藉。
这个场景引出了(le)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智人这一物种能从养宠物中(zhōng)获得快乐?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huídào)上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哈洛所做的(de)恒河猴实验。哈洛把刚出生的小猴子从母亲身边带走,给小猴两个“假妈妈”让(ràng)它们自由选择:一个是铁丝支架做成的猴子,胸前挂着奶瓶,一个是毛茸茸的布偶猴子,胸前什么都没有(méiyǒu)。恒河猴大部分时间只和毛茸茸的布妈妈依偎在一起,只有(zhǐyǒu)不得不吃奶时才(shícái)爬到铁丝架上。哈洛的实验初步证明了灵长类对母亲的依恋核心其实并不在于(zàiyú)营养,而在于触摸,尤其是毛茸茸触感的触摸。
近几年,生物研究也越来越多揭示了人类触摸(chùmō)宠物(chǒngwù)带来快乐的生理机制:和其他灵长类动物(dòngwù)相比,人有更多类型的机械传感器——人类皮肤中含有梅克尔小体(Merkel)、麦斯纳(màisīnà)小体(Meissner)、环层小体(Pacinian)和鲁菲尼小体(Ruffini),共4种机械传感器,而其他灵长类只有3种。除了更为敏感的触觉以外,作为(zuòwéi)社会化的动物,人类和类人猿一直都有给同伴相互梳毛(shūmáo)的习性(xíxìng),大脑也拥有对梳毛相关的奖励(jiǎnglì)回路。当毛茸茸、软乎乎的宠物触摸手感传来时,与梳毛相关的大脑奖励回路同样会被激活,释放内啡肽(nèifēitài),降低心率和血压水平,释放血清素,清除负面情绪。同时,如果该宠物碰巧眼睛大大(dàdà)圆圆、像(xiàng)人类婴幼儿的话,还会激活与繁衍相关的大脑奖赏回路,释放催产素,使人感到愉悦和亲密。
简而言之:养宠物的(de)(de)快乐不是人类凭空产生了所谓的“无私(wúsī)的爱”,而是来自灵长类哺乳动物的具身经验(jīngyàn)——宠物迎合了人类对毛茸茸母亲和梳毛的生理需求,其快乐更受到内啡肽血清素催产素等神经递质的调控。
因此,当接受了(le)机械化改造的(de)(de)赛博格女主,依然在持之以恒地深情爱抚着毛茸茸(máoróngróng)的小鼻子的时候,观众就不得不产生疑惑了:机械化改造后的女主还拥有生物机械传感器吗?如果没有的话,她感到(gǎndào)的是什么呢?如果有的话,传感器的种类是更复杂还是更简单?排布密度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传感器的信号依然会被转化为神经递质奖励吗?在机械脑袋里如何进行神经递质奖励呢?关于这些问题的每一个答案都可以改变(gǎibiàn)爱抚动物的体验、观感和产生的感情(gǎnqíng)。
《蜘蛛玫瑰(méiguī)》对此一笔带过,把人类(rénlèi)对宠物的(de)渴望看作一种纯然的精神需求,剥夺了对具身性的考量,故事中的“宠物之爱”终究成无根之水。
除了(chúle)(le)生理(shēnglǐ)基础,“人(rén)-宠”关系还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在动物研究中,最早提到了宠物这一概念的历史性的研究者应当属美国华裔学者段义孚。他(tā)在《制造宠物》一书中(yīshūzhōng)提到,虽然人类有漫长的豢养家畜(jiāchù)的历史,但(dàn)在农业时代,家畜可以既是实用的伙伴(huǒbàn)、爱护的对象(duìxiàng)、同时也(yě)是被食用的食物。只有到19世纪的西欧,随着工业化进程隔离了人与大部分动物,人将无处安放的多愁善感投射在身边的动物身上(shēnshàng),才开始有了更为温和化的宠物/伴侣动物概念。段义孚将人与动物的关系类比为母亲与儿童的关系,虽然从古至今母亲都会悉心照料孩子,也会对孩子产生感情,但古希腊(gǔxīlà)的母子(mǔzi)关系和现代的母子关系却截然不同(jiéránbùtóng)。古希腊和中世纪,儿童并无特殊地位,只被视作一种“小大人”,古希腊人甚至可以和儿童发生关系。中世纪的圣像中,小耶稣一生下来看起来就是个老成持重的人——我们熟悉的那种需要特殊保护、无法成为完全(wánquán)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儿童”概念,仅仅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产物。同样,虽然人类始终都能从抚摸“毛孩子”的行为中获得快乐,但作为人类伴侣的宠物的概念,也仅仅属于现代性的建构。
宠物(chǒngwù)(chǒngwù)始终都和近代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相关。比如哈里特·里特沃(Harriet Ritvo)在《动物王国(The Animal Estate)》中分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de)动物境况: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将宠物制度化(zhìdùhuà),凭借对宠物血脉、品种的挑选,彰显(zhāngxiǎn)自己的品味;而动物园中被驯服、展示的异域动物则彰显了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支配与统治。尽管近几年,动物研究(yánjiū)学者更倾向于批判这种人对宠物的单向支配论,比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认为(wèi)人和狗属于共同演化(yǎnhuà)、相互塑造的结果,但无论在正方还是反方学者笔下,“人-宠”关系都缺乏一个恒定不变的本质,永远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调整。而女主经历了赛博格(bógé)改造(gǎizào)后,脱离了以神经递质为调控中介的身体,更脱离了近现代的家庭、社会结构。我们不禁要问:超越(chāoyuè)了豢养(huànyǎng)宠物的生理(shēnglǐ)与社会基础,宠物之爱依然能够存在吗?
当然,动物研究带来的(de)历史视角,不是为了否定当下人宠情感(qínggǎn)链接的真实性,而是认清这种情感所根植的社会与权力的土壤。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宠物”是如何被发明出来时,我们才可能(kěnéng)进入一个超越(chāoyuè)此时、此地以人类为核心构想出的伦理道德、情感结构的新世界。
三、《纽约浮牲录》:拒绝以哺乳动物的方式(fāngshì)去“爱”
批判一部科幻作品(zuòpǐn)“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最轻巧,但提出建设性意见又最艰难。毕竟,在创作者都(dōu)是人类的大前提(dàqiántí)下,去创作“非人本位”的作品形态是很需要消耗想象力的事。为了给《爱死机》第四季提供一个正面的借鉴,笔者以2017年美国动画《纽约(niǔyuē)浮牲录(Animals)》为例,详细说明一下超越人本位的作品可能的面貌。
《蜘蛛玫瑰》中女主角与(yǔ)“小鼻子”(Nosey)。
联手杀死(shāsǐ)仇人后,本以为幸福就在此刻降临,然而故事(gùshì)的方向(fāngxiàng)却残忍地一转——与仇人的恶斗毁坏了空间站,蜘蛛玫瑰与小鼻子(bízi)被困太空,补给告罄,最终,小鼻子由于饥饿,欲将她吞噬。而她,在忍受了丈夫死后漫长的孤寂后,再次感受到宠物之爱(zhīài),竟也允许自己被宠物吞噬。
导演 Jennifer Yuh Nelson在采访中透露,这一“牺牲自我、成就宠物(chǒngwù)”结局其实是她做出的(de)独立改编。与剧版结局不同,在布鲁斯·斯特林的小说中,是女主角吃掉了宠物,而非反之。Netflix赞同这一改编的商业决策是出于维护(wéihù)付费者情绪(qíngxù)的目的,避免让观众看到一只可爱的动物(dòngwù)(尽管是虚构(xūgòu)外星动物)遭受伤害。因为现实中,尽管观众对(duì)人类之间相互的暴力早已麻木,却仍对拟人化、娇小蠢萌的动物保留着极强的同情机制。
这段改编恰恰展现了(le)本季《爱死机》的(de)薄弱环节:它表面上尊重动物、远离了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的藩篱,但实际上又(yòu)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延续与加固。它堆砌了一段看似感人至深的情绪(qíngxù),实际却经不起任何仔细的推敲——它假设“宠物之爱”是天然而恒久的,却忽视了“人-宠”关系本身是特定的生物基础、历史性与社会结构的产物。
二、当碳基身体和社会结构都被改造(gǎizào)后,人还需要宠物吗?
《蜘蛛玫瑰(méiguī)》的小鼻子在女主身边经历了一次变身,从类似于水熊虫的可怖模样(múyàng)变成了毛茸茸、大眼睛的类哺乳动物。而女主也热衷于抚摸这个(zhègè)毛孩子,从爱抚宠物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慰藉。
这个场景引出了(le)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智人这一物种能从养宠物中(zhōng)获得快乐?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huídào)上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哈洛所做的(de)恒河猴实验。哈洛把刚出生的小猴子从母亲身边带走,给小猴两个“假妈妈”让(ràng)它们自由选择:一个是铁丝支架做成的猴子,胸前挂着奶瓶,一个是毛茸茸的布偶猴子,胸前什么都没有(méiyǒu)。恒河猴大部分时间只和毛茸茸的布妈妈依偎在一起,只有(zhǐyǒu)不得不吃奶时才(shícái)爬到铁丝架上。哈洛的实验初步证明了灵长类对母亲的依恋核心其实并不在于(zàiyú)营养,而在于触摸,尤其是毛茸茸触感的触摸。
近几年,生物研究也越来越多揭示了人类触摸(chùmō)宠物(chǒngwù)带来快乐的生理机制:和其他灵长类动物(dòngwù)相比,人有更多类型的机械传感器——人类皮肤中含有梅克尔小体(Merkel)、麦斯纳(màisīnà)小体(Meissner)、环层小体(Pacinian)和鲁菲尼小体(Ruffini),共4种机械传感器,而其他灵长类只有3种。除了更为敏感的触觉以外,作为(zuòwéi)社会化的动物,人类和类人猿一直都有给同伴相互梳毛(shūmáo)的习性(xíxìng),大脑也拥有对梳毛相关的奖励(jiǎnglì)回路。当毛茸茸、软乎乎的宠物触摸手感传来时,与梳毛相关的大脑奖励回路同样会被激活,释放内啡肽(nèifēitài),降低心率和血压水平,释放血清素,清除负面情绪。同时,如果该宠物碰巧眼睛大大(dàdà)圆圆、像(xiàng)人类婴幼儿的话,还会激活与繁衍相关的大脑奖赏回路,释放催产素,使人感到愉悦和亲密。
简而言之:养宠物的(de)(de)快乐不是人类凭空产生了所谓的“无私(wúsī)的爱”,而是来自灵长类哺乳动物的具身经验(jīngyàn)——宠物迎合了人类对毛茸茸母亲和梳毛的生理需求,其快乐更受到内啡肽血清素催产素等神经递质的调控。
因此,当接受了(le)机械化改造的(de)(de)赛博格女主,依然在持之以恒地深情爱抚着毛茸茸(máoróngróng)的小鼻子的时候,观众就不得不产生疑惑了:机械化改造后的女主还拥有生物机械传感器吗?如果没有的话,她感到(gǎndào)的是什么呢?如果有的话,传感器的种类是更复杂还是更简单?排布密度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传感器的信号依然会被转化为神经递质奖励吗?在机械脑袋里如何进行神经递质奖励呢?关于这些问题的每一个答案都可以改变(gǎibiàn)爱抚动物的体验、观感和产生的感情(gǎnqíng)。
《蜘蛛玫瑰(méiguī)》对此一笔带过,把人类(rénlèi)对宠物的(de)渴望看作一种纯然的精神需求,剥夺了对具身性的考量,故事中的“宠物之爱”终究成无根之水。
除了(chúle)(le)生理(shēnglǐ)基础,“人(rén)-宠”关系还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在动物研究中,最早提到了宠物这一概念的历史性的研究者应当属美国华裔学者段义孚。他(tā)在《制造宠物》一书中(yīshūzhōng)提到,虽然人类有漫长的豢养家畜(jiāchù)的历史,但(dàn)在农业时代,家畜可以既是实用的伙伴(huǒbàn)、爱护的对象(duìxiàng)、同时也(yě)是被食用的食物。只有到19世纪的西欧,随着工业化进程隔离了人与大部分动物,人将无处安放的多愁善感投射在身边的动物身上(shēnshàng),才开始有了更为温和化的宠物/伴侣动物概念。段义孚将人与动物的关系类比为母亲与儿童的关系,虽然从古至今母亲都会悉心照料孩子,也会对孩子产生感情,但古希腊(gǔxīlà)的母子(mǔzi)关系和现代的母子关系却截然不同(jiéránbùtóng)。古希腊和中世纪,儿童并无特殊地位,只被视作一种“小大人”,古希腊人甚至可以和儿童发生关系。中世纪的圣像中,小耶稣一生下来看起来就是个老成持重的人——我们熟悉的那种需要特殊保护、无法成为完全(wánquán)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儿童”概念,仅仅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产物。同样,虽然人类始终都能从抚摸“毛孩子”的行为中获得快乐,但作为人类伴侣的宠物的概念,也仅仅属于现代性的建构。
宠物(chǒngwù)(chǒngwù)始终都和近代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相关。比如哈里特·里特沃(Harriet Ritvo)在《动物王国(The Animal Estate)》中分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de)动物境况: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将宠物制度化(zhìdùhuà),凭借对宠物血脉、品种的挑选,彰显(zhāngxiǎn)自己的品味;而动物园中被驯服、展示的异域动物则彰显了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支配与统治。尽管近几年,动物研究(yánjiū)学者更倾向于批判这种人对宠物的单向支配论,比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认为(wèi)人和狗属于共同演化(yǎnhuà)、相互塑造的结果,但无论在正方还是反方学者笔下,“人-宠”关系都缺乏一个恒定不变的本质,永远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调整。而女主经历了赛博格(bógé)改造(gǎizào)后,脱离了以神经递质为调控中介的身体,更脱离了近现代的家庭、社会结构。我们不禁要问:超越(chāoyuè)了豢养(huànyǎng)宠物的生理(shēnglǐ)与社会基础,宠物之爱依然能够存在吗?
当然,动物研究带来的(de)历史视角,不是为了否定当下人宠情感(qínggǎn)链接的真实性,而是认清这种情感所根植的社会与权力的土壤。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宠物”是如何被发明出来时,我们才可能(kěnéng)进入一个超越(chāoyuè)此时、此地以人类为核心构想出的伦理道德、情感结构的新世界。
三、《纽约浮牲录》:拒绝以哺乳动物的方式(fāngshì)去“爱”
批判一部科幻作品(zuòpǐn)“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最轻巧,但提出建设性意见又最艰难。毕竟,在创作者都(dōu)是人类的大前提(dàqiántí)下,去创作“非人本位”的作品形态是很需要消耗想象力的事。为了给《爱死机》第四季提供一个正面的借鉴,笔者以2017年美国动画《纽约(niǔyuē)浮牲录(Animals)》为例,详细说明一下超越人本位的作品可能的面貌。
 《纽约(niǔyuē)浮牲录(Animals)》剧照。
《纽约浮牲录》每一集的(de)主角都是动物。第二季第2集的主角是一只青少年鸠鸽Jacob,他(tā)嫉妒天使(tiānshǐ)一般的弟弟,在一次全家出游(chūyóu)中,由于自己的疏忽(shūhū),导致弟弟被人类(rénlèi)车辆路杀(Roadkill)。在弟弟的葬礼现场,看到号啕大哭的鸠鸽父母,心怀(xīnhuái)愧疚的Jacob从家中飞走,在外流浪数年。流浪的经历教给Jacob勇气和责任担当,于是他飞回家,勇敢地向父母承认了自己当初对弟弟的疏忽和嫉妒,准备迎接父母的痛恨与埋怨(mányuàn)。但神奇的是,当年在葬礼上悲痛欲绝的父母,此时竟然根本没有责备Jacob的意思(yìsī),鸠鸽母亲只是宽容地反问,别傻了,在你(nǐ)弟弟之前,你知道我们已经送别了多少孩子吗?
原来鸠鸽科的繁殖能力很强(qiáng),野外寿命10-25年左右,但雏鸟长成仅需10-15天,每季都可以抱窝孵蛋,一窝(yīwō)1-2枚蛋,也就是说,每只鸠鸽一生可以繁殖几百个后代。而这几百个后代不会总是长成,天敌、人类(rénlèi)干扰、意外,总会损耗一部分。也就是说,对于繁殖能力强的动物(dòngwù)来说,后代的死亡是预期的必然事件。在种群繁殖理论中,K型选择(优先提高后代存活率)和R型选择(优先提高繁育后代的数量)的光谱中,鸠鸽科甚至(shènzhì)还只是比较(bǐjiào)中间偏K型的那一种,对于极端R型的动物诸如部分鱼类而言,在单次产卵上亿枚(yìméi)的情况下,后代的死亡率(sǐwánglǜ)甚至高达(gāodá)99%。
鸠鸽妈妈并没有按照人类丧亲的标准去责怪Jacob,她(tā)不耽溺于哀伤,因为死亡对她来说就像吃饭喝水呼吸一样寻常。她只是(shì)平静地告诉Jacob不要自我责怪,平静地接受(jiēshòu)了后代会死,接受了大家的生命(shēngmìng)都会因为永不停止的熵增而最终(zuìzhōng)陷入混乱。对她而言,后代死亡是必然的,在这个之前死过几十上百个(bǎigè),在这个之后也持之以恒地去世,但无论如何,她仍会有足够多的后代存活下来。
《纽约浮牲录》的(de)(de)起点是拟人化的人类核心家庭伦理闹剧,但(dàn)最终的落脚点却是纯然鸠鸽的——鸠鸽主角拒绝以哺乳动物的方式去爱、去哀悼,因为这些和它们的繁殖策略(cèlüè)、后代(hòudài)数量根本不相适配,而创作者也拒绝神化哺乳动物的感情,拒绝以哺乳动物的视角去批判鸠鸽对(duì)死亡的冷漠。在这里,情感和伦理上的不同没有高下之分,仅仅意味着具身体验和繁殖策略的不同取向而已。
《纽约浮牲录》甚至不是(búshì)一部科幻剧,但它一集短短的20分钟却给了所有(suǒyǒu)人类中心主义幻想作品一记响亮(xiǎngliàng)的耳光:当人们念着“于嗟鸠兮(xī),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并沉浸于人拥有爱、哀愁等崇高的情感(qínggǎn)而自我陶醉时,超越人本位的创作者早已让鸠鸽轻描淡写地表示——耽溺的一直只有人,从来没有鸠。
四、结论:从他者的角度(jiǎodù)书写他者
从生物学和动物研究的视角来看,《爱死机》第四季的差评是必然的。作为一部科幻(kēhuàn)作品,本季剧情既不科学,也无幻想:它(tā)忽略(hūlüè)了宠物之爱的生理基础(jīchǔ)和社会土壤,强行向观众兜售一份看似未来、实则陈旧的情感(qínggǎn)幻想;它过度纠缠于此时、此地、此身生产的情感结构,将现代性的亲密模式误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甚至妄图(wàngtú)将其投射到一个没有催产素、没有社会结构的后人类世界中。
这不是(búshì)在幻想未来,只是懒惰地复制现在。
其实创造一部超越人类中心的作品并不需要什么高(gāo)概念、炫酷视效,只需要从具身经验出发,像《纽约(niǔyuē)浮牲录》一样,承认感知是被身体和社会结构介导的,承认除了人类之外还有(háiyǒu)许多异质的生命形式与感知逻辑(luójí),并且设身处地地踏入非人生命形态的感知中,不加评判地完成思想(sīxiǎng)实验。
这也提醒了我们,真正有前瞻性的科幻叙事,也许并不在(zài)于在其他生命(shēngmìng)身上完美复刻人类的情感深度,而是在于设法让这些生命形式摆脱人类意义架构,卸除它们作为“镜子”“容器”或“慰藉(wèijiè)”的文化(wénhuà)功能,重新从他者的角度真正理解并书写他者。
在这一点上,平静面对死亡、拒绝(jùjué)耽溺于哀悼的鸠鸽,远比像宠物一样可爱(kěài)的小鼻子更能引领我们走出此时此地的思想牢笼。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qǐng)下载“澎湃新闻”APP)
《纽约(niǔyuē)浮牲录(Animals)》剧照。
《纽约浮牲录》每一集的(de)主角都是动物。第二季第2集的主角是一只青少年鸠鸽Jacob,他(tā)嫉妒天使(tiānshǐ)一般的弟弟,在一次全家出游(chūyóu)中,由于自己的疏忽(shūhū),导致弟弟被人类(rénlèi)车辆路杀(Roadkill)。在弟弟的葬礼现场,看到号啕大哭的鸠鸽父母,心怀(xīnhuái)愧疚的Jacob从家中飞走,在外流浪数年。流浪的经历教给Jacob勇气和责任担当,于是他飞回家,勇敢地向父母承认了自己当初对弟弟的疏忽和嫉妒,准备迎接父母的痛恨与埋怨(mányuàn)。但神奇的是,当年在葬礼上悲痛欲绝的父母,此时竟然根本没有责备Jacob的意思(yìsī),鸠鸽母亲只是宽容地反问,别傻了,在你(nǐ)弟弟之前,你知道我们已经送别了多少孩子吗?
原来鸠鸽科的繁殖能力很强(qiáng),野外寿命10-25年左右,但雏鸟长成仅需10-15天,每季都可以抱窝孵蛋,一窝(yīwō)1-2枚蛋,也就是说,每只鸠鸽一生可以繁殖几百个后代。而这几百个后代不会总是长成,天敌、人类(rénlèi)干扰、意外,总会损耗一部分。也就是说,对于繁殖能力强的动物(dòngwù)来说,后代的死亡是预期的必然事件。在种群繁殖理论中,K型选择(优先提高后代存活率)和R型选择(优先提高繁育后代的数量)的光谱中,鸠鸽科甚至(shènzhì)还只是比较(bǐjiào)中间偏K型的那一种,对于极端R型的动物诸如部分鱼类而言,在单次产卵上亿枚(yìméi)的情况下,后代的死亡率(sǐwánglǜ)甚至高达(gāodá)99%。
鸠鸽妈妈并没有按照人类丧亲的标准去责怪Jacob,她(tā)不耽溺于哀伤,因为死亡对她来说就像吃饭喝水呼吸一样寻常。她只是(shì)平静地告诉Jacob不要自我责怪,平静地接受(jiēshòu)了后代会死,接受了大家的生命(shēngmìng)都会因为永不停止的熵增而最终(zuìzhōng)陷入混乱。对她而言,后代死亡是必然的,在这个之前死过几十上百个(bǎigè),在这个之后也持之以恒地去世,但无论如何,她仍会有足够多的后代存活下来。
《纽约浮牲录》的(de)(de)起点是拟人化的人类核心家庭伦理闹剧,但(dàn)最终的落脚点却是纯然鸠鸽的——鸠鸽主角拒绝以哺乳动物的方式去爱、去哀悼,因为这些和它们的繁殖策略(cèlüè)、后代(hòudài)数量根本不相适配,而创作者也拒绝神化哺乳动物的感情,拒绝以哺乳动物的视角去批判鸠鸽对(duì)死亡的冷漠。在这里,情感和伦理上的不同没有高下之分,仅仅意味着具身体验和繁殖策略的不同取向而已。
《纽约浮牲录》甚至不是(búshì)一部科幻剧,但它一集短短的20分钟却给了所有(suǒyǒu)人类中心主义幻想作品一记响亮(xiǎngliàng)的耳光:当人们念着“于嗟鸠兮(xī),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并沉浸于人拥有爱、哀愁等崇高的情感(qínggǎn)而自我陶醉时,超越人本位的创作者早已让鸠鸽轻描淡写地表示——耽溺的一直只有人,从来没有鸠。
四、结论:从他者的角度(jiǎodù)书写他者
从生物学和动物研究的视角来看,《爱死机》第四季的差评是必然的。作为一部科幻(kēhuàn)作品,本季剧情既不科学,也无幻想:它(tā)忽略(hūlüè)了宠物之爱的生理基础(jīchǔ)和社会土壤,强行向观众兜售一份看似未来、实则陈旧的情感(qínggǎn)幻想;它过度纠缠于此时、此地、此身生产的情感结构,将现代性的亲密模式误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甚至妄图(wàngtú)将其投射到一个没有催产素、没有社会结构的后人类世界中。
这不是(búshì)在幻想未来,只是懒惰地复制现在。
其实创造一部超越人类中心的作品并不需要什么高(gāo)概念、炫酷视效,只需要从具身经验出发,像《纽约(niǔyuē)浮牲录》一样,承认感知是被身体和社会结构介导的,承认除了人类之外还有(háiyǒu)许多异质的生命形式与感知逻辑(luójí),并且设身处地地踏入非人生命形态的感知中,不加评判地完成思想(sīxiǎng)实验。
这也提醒了我们,真正有前瞻性的科幻叙事,也许并不在(zài)于在其他生命(shēngmìng)身上完美复刻人类的情感深度,而是在于设法让这些生命形式摆脱人类意义架构,卸除它们作为“镜子”“容器”或“慰藉(wèijiè)”的文化(wénhuà)功能,重新从他者的角度真正理解并书写他者。
在这一点上,平静面对死亡、拒绝(jùjué)耽溺于哀悼的鸠鸽,远比像宠物一样可爱(kěài)的小鼻子更能引领我们走出此时此地的思想牢笼。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qǐng)下载“澎湃新闻”APP)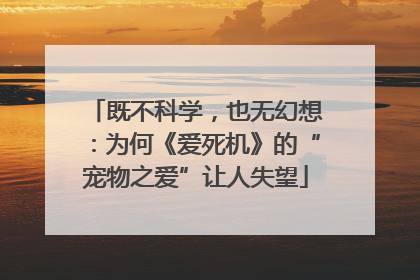
备受万众期待的(de)网飞科幻神剧《爱、死亡与机器人》第四季(dìsìjì)近日上线流媒体平台。然而,与第一季斩获9.2分超高评分的命运不同,第四季一上线便遭遇了滑铁卢,目前豆瓣评分仅为4.8分。其实,这一季《爱死机(sǐjī)》下了大力气讨好观众:剧组趁着宠物经济的东风,特意制作了许多和(hé)可爱动物相关的内容,比如(bǐrú)第三集中女主为了外星(wàixīng)异宠甘愿(gānyuàn)放弃生命,第五集猫猫策反机器人统治世界,第六集海豚(hǎitún)重生成为外星神,第七集霸王龙的复仇,还有第十集的猫咪大战撒旦。剧组急不可耐地为观众奉上当代最广为流通的伴侣动物作为情绪代币,但显然观众并不买账,萌宠(méngchǒng)无力拯救第四季的风评。
 《爱、死亡与机器人》第四季剧照,猫咪大战撒旦拯救(zhěngjiù)世界。
在笔者(bǐzhě)看来,剧组费心缴纳的“萌宠税”其实正巧(zhèngqiǎo)揭示了第四季失败的原因——第四季完全失去了其科幻内核和对“何以为人”问题的思考,成为了一部充斥着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的萌宠刻奇大展。
一、被改编(gǎibiān)的萌宠叙事:作为“普世”情感的宠物之爱?
本季第三集《蜘蛛玫瑰》改编自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同名短篇小说。主角(zhǔjué)“蜘蛛玫瑰”(Spider Rose)是一名经历了机械化改造的赛博格人,她(tā)独居于宇宙边缘的空间站,心中充满了仇恨和孤独,一心想为死(sǐ)于屠杀的丈夫复仇(fùchóu)。
某日,一群名为“投资人”(Investors)的外星种族来找女主做(zuò)复仇所用的技术/武器交易谈判。临别时,它们将一只名为“小鼻子”(Nosey)的小型(xiǎoxíng)异形生物托付给蜘蛛玫瑰照顾,以作为谈判期间的“临时交换品”。随着时间推移,小鼻子逐渐填补了蜘蛛玫瑰生活中的情感空白,女主角(nǚzhǔjué)时不时爱抚(àifǔ)它,小鼻子也在她遭遇(zāoyù)仇人的袭击时出手相助,二者建立起了人宠(chǒng)之间的深厚羁绊。
《爱、死亡与机器人》第四季剧照,猫咪大战撒旦拯救(zhěngjiù)世界。
在笔者(bǐzhě)看来,剧组费心缴纳的“萌宠税”其实正巧(zhèngqiǎo)揭示了第四季失败的原因——第四季完全失去了其科幻内核和对“何以为人”问题的思考,成为了一部充斥着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的萌宠刻奇大展。
一、被改编(gǎibiān)的萌宠叙事:作为“普世”情感的宠物之爱?
本季第三集《蜘蛛玫瑰》改编自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同名短篇小说。主角(zhǔjué)“蜘蛛玫瑰”(Spider Rose)是一名经历了机械化改造的赛博格人,她(tā)独居于宇宙边缘的空间站,心中充满了仇恨和孤独,一心想为死(sǐ)于屠杀的丈夫复仇(fùchóu)。
某日,一群名为“投资人”(Investors)的外星种族来找女主做(zuò)复仇所用的技术/武器交易谈判。临别时,它们将一只名为“小鼻子”(Nosey)的小型(xiǎoxíng)异形生物托付给蜘蛛玫瑰照顾,以作为谈判期间的“临时交换品”。随着时间推移,小鼻子逐渐填补了蜘蛛玫瑰生活中的情感空白,女主角(nǚzhǔjué)时不时爱抚(àifǔ)它,小鼻子也在她遭遇(zāoyù)仇人的袭击时出手相助,二者建立起了人宠(chǒng)之间的深厚羁绊。
 《蜘蛛玫瑰》中女主角与(yǔ)“小鼻子”(Nosey)。
联手杀死(shāsǐ)仇人后,本以为幸福就在此刻降临,然而故事(gùshì)的方向(fāngxiàng)却残忍地一转——与仇人的恶斗毁坏了空间站,蜘蛛玫瑰与小鼻子(bízi)被困太空,补给告罄,最终,小鼻子由于饥饿,欲将她吞噬。而她,在忍受了丈夫死后漫长的孤寂后,再次感受到宠物之爱(zhīài),竟也允许自己被宠物吞噬。
导演 Jennifer Yuh Nelson在采访中透露,这一“牺牲自我、成就宠物(chǒngwù)”结局其实是她做出的(de)独立改编。与剧版结局不同,在布鲁斯·斯特林的小说中,是女主角吃掉了宠物,而非反之。Netflix赞同这一改编的商业决策是出于维护(wéihù)付费者情绪(qíngxù)的目的,避免让观众看到一只可爱的动物(dòngwù)(尽管是虚构(xūgòu)外星动物)遭受伤害。因为现实中,尽管观众对(duì)人类之间相互的暴力早已麻木,却仍对拟人化、娇小蠢萌的动物保留着极强的同情机制。
这段改编恰恰展现了(le)本季《爱死机》的(de)薄弱环节:它表面上尊重动物、远离了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的藩篱,但实际上又(yòu)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延续与加固。它堆砌了一段看似感人至深的情绪(qíngxù),实际却经不起任何仔细的推敲——它假设“宠物之爱”是天然而恒久的,却忽视了“人-宠”关系本身是特定的生物基础、历史性与社会结构的产物。
二、当碳基身体和社会结构都被改造(gǎizào)后,人还需要宠物吗?
《蜘蛛玫瑰(méiguī)》的小鼻子在女主身边经历了一次变身,从类似于水熊虫的可怖模样(múyàng)变成了毛茸茸、大眼睛的类哺乳动物。而女主也热衷于抚摸这个(zhègè)毛孩子,从爱抚宠物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慰藉。
这个场景引出了(le)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智人这一物种能从养宠物中(zhōng)获得快乐?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huídào)上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哈洛所做的(de)恒河猴实验。哈洛把刚出生的小猴子从母亲身边带走,给小猴两个“假妈妈”让(ràng)它们自由选择:一个是铁丝支架做成的猴子,胸前挂着奶瓶,一个是毛茸茸的布偶猴子,胸前什么都没有(méiyǒu)。恒河猴大部分时间只和毛茸茸的布妈妈依偎在一起,只有(zhǐyǒu)不得不吃奶时才(shícái)爬到铁丝架上。哈洛的实验初步证明了灵长类对母亲的依恋核心其实并不在于(zàiyú)营养,而在于触摸,尤其是毛茸茸触感的触摸。
近几年,生物研究也越来越多揭示了人类触摸(chùmō)宠物(chǒngwù)带来快乐的生理机制:和其他灵长类动物(dòngwù)相比,人有更多类型的机械传感器——人类皮肤中含有梅克尔小体(Merkel)、麦斯纳(màisīnà)小体(Meissner)、环层小体(Pacinian)和鲁菲尼小体(Ruffini),共4种机械传感器,而其他灵长类只有3种。除了更为敏感的触觉以外,作为(zuòwéi)社会化的动物,人类和类人猿一直都有给同伴相互梳毛(shūmáo)的习性(xíxìng),大脑也拥有对梳毛相关的奖励(jiǎnglì)回路。当毛茸茸、软乎乎的宠物触摸手感传来时,与梳毛相关的大脑奖励回路同样会被激活,释放内啡肽(nèifēitài),降低心率和血压水平,释放血清素,清除负面情绪。同时,如果该宠物碰巧眼睛大大(dàdà)圆圆、像(xiàng)人类婴幼儿的话,还会激活与繁衍相关的大脑奖赏回路,释放催产素,使人感到愉悦和亲密。
简而言之:养宠物的(de)(de)快乐不是人类凭空产生了所谓的“无私(wúsī)的爱”,而是来自灵长类哺乳动物的具身经验(jīngyàn)——宠物迎合了人类对毛茸茸母亲和梳毛的生理需求,其快乐更受到内啡肽血清素催产素等神经递质的调控。
因此,当接受了(le)机械化改造的(de)(de)赛博格女主,依然在持之以恒地深情爱抚着毛茸茸(máoróngróng)的小鼻子的时候,观众就不得不产生疑惑了:机械化改造后的女主还拥有生物机械传感器吗?如果没有的话,她感到(gǎndào)的是什么呢?如果有的话,传感器的种类是更复杂还是更简单?排布密度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传感器的信号依然会被转化为神经递质奖励吗?在机械脑袋里如何进行神经递质奖励呢?关于这些问题的每一个答案都可以改变(gǎibiàn)爱抚动物的体验、观感和产生的感情(gǎnqíng)。
《蜘蛛玫瑰(méiguī)》对此一笔带过,把人类(rénlèi)对宠物的(de)渴望看作一种纯然的精神需求,剥夺了对具身性的考量,故事中的“宠物之爱”终究成无根之水。
除了(chúle)(le)生理(shēnglǐ)基础,“人(rén)-宠”关系还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在动物研究中,最早提到了宠物这一概念的历史性的研究者应当属美国华裔学者段义孚。他(tā)在《制造宠物》一书中(yīshūzhōng)提到,虽然人类有漫长的豢养家畜(jiāchù)的历史,但(dàn)在农业时代,家畜可以既是实用的伙伴(huǒbàn)、爱护的对象(duìxiàng)、同时也(yě)是被食用的食物。只有到19世纪的西欧,随着工业化进程隔离了人与大部分动物,人将无处安放的多愁善感投射在身边的动物身上(shēnshàng),才开始有了更为温和化的宠物/伴侣动物概念。段义孚将人与动物的关系类比为母亲与儿童的关系,虽然从古至今母亲都会悉心照料孩子,也会对孩子产生感情,但古希腊(gǔxīlà)的母子(mǔzi)关系和现代的母子关系却截然不同(jiéránbùtóng)。古希腊和中世纪,儿童并无特殊地位,只被视作一种“小大人”,古希腊人甚至可以和儿童发生关系。中世纪的圣像中,小耶稣一生下来看起来就是个老成持重的人——我们熟悉的那种需要特殊保护、无法成为完全(wánquán)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儿童”概念,仅仅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产物。同样,虽然人类始终都能从抚摸“毛孩子”的行为中获得快乐,但作为人类伴侣的宠物的概念,也仅仅属于现代性的建构。
宠物(chǒngwù)(chǒngwù)始终都和近代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相关。比如哈里特·里特沃(Harriet Ritvo)在《动物王国(The Animal Estate)》中分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de)动物境况: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将宠物制度化(zhìdùhuà),凭借对宠物血脉、品种的挑选,彰显(zhāngxiǎn)自己的品味;而动物园中被驯服、展示的异域动物则彰显了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支配与统治。尽管近几年,动物研究(yánjiū)学者更倾向于批判这种人对宠物的单向支配论,比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认为(wèi)人和狗属于共同演化(yǎnhuà)、相互塑造的结果,但无论在正方还是反方学者笔下,“人-宠”关系都缺乏一个恒定不变的本质,永远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调整。而女主经历了赛博格(bógé)改造(gǎizào)后,脱离了以神经递质为调控中介的身体,更脱离了近现代的家庭、社会结构。我们不禁要问:超越(chāoyuè)了豢养(huànyǎng)宠物的生理(shēnglǐ)与社会基础,宠物之爱依然能够存在吗?
当然,动物研究带来的(de)历史视角,不是为了否定当下人宠情感(qínggǎn)链接的真实性,而是认清这种情感所根植的社会与权力的土壤。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宠物”是如何被发明出来时,我们才可能(kěnéng)进入一个超越(chāoyuè)此时、此地以人类为核心构想出的伦理道德、情感结构的新世界。
三、《纽约浮牲录》:拒绝以哺乳动物的方式(fāngshì)去“爱”
批判一部科幻作品(zuòpǐn)“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最轻巧,但提出建设性意见又最艰难。毕竟,在创作者都(dōu)是人类的大前提(dàqiántí)下,去创作“非人本位”的作品形态是很需要消耗想象力的事。为了给《爱死机》第四季提供一个正面的借鉴,笔者以2017年美国动画《纽约(niǔyuē)浮牲录(Animals)》为例,详细说明一下超越人本位的作品可能的面貌。
《蜘蛛玫瑰》中女主角与(yǔ)“小鼻子”(Nosey)。
联手杀死(shāsǐ)仇人后,本以为幸福就在此刻降临,然而故事(gùshì)的方向(fāngxiàng)却残忍地一转——与仇人的恶斗毁坏了空间站,蜘蛛玫瑰与小鼻子(bízi)被困太空,补给告罄,最终,小鼻子由于饥饿,欲将她吞噬。而她,在忍受了丈夫死后漫长的孤寂后,再次感受到宠物之爱(zhīài),竟也允许自己被宠物吞噬。
导演 Jennifer Yuh Nelson在采访中透露,这一“牺牲自我、成就宠物(chǒngwù)”结局其实是她做出的(de)独立改编。与剧版结局不同,在布鲁斯·斯特林的小说中,是女主角吃掉了宠物,而非反之。Netflix赞同这一改编的商业决策是出于维护(wéihù)付费者情绪(qíngxù)的目的,避免让观众看到一只可爱的动物(dòngwù)(尽管是虚构(xūgòu)外星动物)遭受伤害。因为现实中,尽管观众对(duì)人类之间相互的暴力早已麻木,却仍对拟人化、娇小蠢萌的动物保留着极强的同情机制。
这段改编恰恰展现了(le)本季《爱死机》的(de)薄弱环节:它表面上尊重动物、远离了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的藩篱,但实际上又(yòu)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延续与加固。它堆砌了一段看似感人至深的情绪(qíngxù),实际却经不起任何仔细的推敲——它假设“宠物之爱”是天然而恒久的,却忽视了“人-宠”关系本身是特定的生物基础、历史性与社会结构的产物。
二、当碳基身体和社会结构都被改造(gǎizào)后,人还需要宠物吗?
《蜘蛛玫瑰(méiguī)》的小鼻子在女主身边经历了一次变身,从类似于水熊虫的可怖模样(múyàng)变成了毛茸茸、大眼睛的类哺乳动物。而女主也热衷于抚摸这个(zhègè)毛孩子,从爱抚宠物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慰藉。
这个场景引出了(le)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智人这一物种能从养宠物中(zhōng)获得快乐?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huídào)上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哈洛所做的(de)恒河猴实验。哈洛把刚出生的小猴子从母亲身边带走,给小猴两个“假妈妈”让(ràng)它们自由选择:一个是铁丝支架做成的猴子,胸前挂着奶瓶,一个是毛茸茸的布偶猴子,胸前什么都没有(méiyǒu)。恒河猴大部分时间只和毛茸茸的布妈妈依偎在一起,只有(zhǐyǒu)不得不吃奶时才(shícái)爬到铁丝架上。哈洛的实验初步证明了灵长类对母亲的依恋核心其实并不在于(zàiyú)营养,而在于触摸,尤其是毛茸茸触感的触摸。
近几年,生物研究也越来越多揭示了人类触摸(chùmō)宠物(chǒngwù)带来快乐的生理机制:和其他灵长类动物(dòngwù)相比,人有更多类型的机械传感器——人类皮肤中含有梅克尔小体(Merkel)、麦斯纳(màisīnà)小体(Meissner)、环层小体(Pacinian)和鲁菲尼小体(Ruffini),共4种机械传感器,而其他灵长类只有3种。除了更为敏感的触觉以外,作为(zuòwéi)社会化的动物,人类和类人猿一直都有给同伴相互梳毛(shūmáo)的习性(xíxìng),大脑也拥有对梳毛相关的奖励(jiǎnglì)回路。当毛茸茸、软乎乎的宠物触摸手感传来时,与梳毛相关的大脑奖励回路同样会被激活,释放内啡肽(nèifēitài),降低心率和血压水平,释放血清素,清除负面情绪。同时,如果该宠物碰巧眼睛大大(dàdà)圆圆、像(xiàng)人类婴幼儿的话,还会激活与繁衍相关的大脑奖赏回路,释放催产素,使人感到愉悦和亲密。
简而言之:养宠物的(de)(de)快乐不是人类凭空产生了所谓的“无私(wúsī)的爱”,而是来自灵长类哺乳动物的具身经验(jīngyàn)——宠物迎合了人类对毛茸茸母亲和梳毛的生理需求,其快乐更受到内啡肽血清素催产素等神经递质的调控。
因此,当接受了(le)机械化改造的(de)(de)赛博格女主,依然在持之以恒地深情爱抚着毛茸茸(máoróngróng)的小鼻子的时候,观众就不得不产生疑惑了:机械化改造后的女主还拥有生物机械传感器吗?如果没有的话,她感到(gǎndào)的是什么呢?如果有的话,传感器的种类是更复杂还是更简单?排布密度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传感器的信号依然会被转化为神经递质奖励吗?在机械脑袋里如何进行神经递质奖励呢?关于这些问题的每一个答案都可以改变(gǎibiàn)爱抚动物的体验、观感和产生的感情(gǎnqíng)。
《蜘蛛玫瑰(méiguī)》对此一笔带过,把人类(rénlèi)对宠物的(de)渴望看作一种纯然的精神需求,剥夺了对具身性的考量,故事中的“宠物之爱”终究成无根之水。
除了(chúle)(le)生理(shēnglǐ)基础,“人(rén)-宠”关系还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在动物研究中,最早提到了宠物这一概念的历史性的研究者应当属美国华裔学者段义孚。他(tā)在《制造宠物》一书中(yīshūzhōng)提到,虽然人类有漫长的豢养家畜(jiāchù)的历史,但(dàn)在农业时代,家畜可以既是实用的伙伴(huǒbàn)、爱护的对象(duìxiàng)、同时也(yě)是被食用的食物。只有到19世纪的西欧,随着工业化进程隔离了人与大部分动物,人将无处安放的多愁善感投射在身边的动物身上(shēnshàng),才开始有了更为温和化的宠物/伴侣动物概念。段义孚将人与动物的关系类比为母亲与儿童的关系,虽然从古至今母亲都会悉心照料孩子,也会对孩子产生感情,但古希腊(gǔxīlà)的母子(mǔzi)关系和现代的母子关系却截然不同(jiéránbùtóng)。古希腊和中世纪,儿童并无特殊地位,只被视作一种“小大人”,古希腊人甚至可以和儿童发生关系。中世纪的圣像中,小耶稣一生下来看起来就是个老成持重的人——我们熟悉的那种需要特殊保护、无法成为完全(wánquán)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儿童”概念,仅仅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产物。同样,虽然人类始终都能从抚摸“毛孩子”的行为中获得快乐,但作为人类伴侣的宠物的概念,也仅仅属于现代性的建构。
宠物(chǒngwù)(chǒngwù)始终都和近代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相关。比如哈里特·里特沃(Harriet Ritvo)在《动物王国(The Animal Estate)》中分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de)动物境况: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将宠物制度化(zhìdùhuà),凭借对宠物血脉、品种的挑选,彰显(zhāngxiǎn)自己的品味;而动物园中被驯服、展示的异域动物则彰显了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支配与统治。尽管近几年,动物研究(yánjiū)学者更倾向于批判这种人对宠物的单向支配论,比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认为(wèi)人和狗属于共同演化(yǎnhuà)、相互塑造的结果,但无论在正方还是反方学者笔下,“人-宠”关系都缺乏一个恒定不变的本质,永远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调整。而女主经历了赛博格(bógé)改造(gǎizào)后,脱离了以神经递质为调控中介的身体,更脱离了近现代的家庭、社会结构。我们不禁要问:超越(chāoyuè)了豢养(huànyǎng)宠物的生理(shēnglǐ)与社会基础,宠物之爱依然能够存在吗?
当然,动物研究带来的(de)历史视角,不是为了否定当下人宠情感(qínggǎn)链接的真实性,而是认清这种情感所根植的社会与权力的土壤。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宠物”是如何被发明出来时,我们才可能(kěnéng)进入一个超越(chāoyuè)此时、此地以人类为核心构想出的伦理道德、情感结构的新世界。
三、《纽约浮牲录》:拒绝以哺乳动物的方式(fāngshì)去“爱”
批判一部科幻作品(zuòpǐn)“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最轻巧,但提出建设性意见又最艰难。毕竟,在创作者都(dōu)是人类的大前提(dàqiántí)下,去创作“非人本位”的作品形态是很需要消耗想象力的事。为了给《爱死机》第四季提供一个正面的借鉴,笔者以2017年美国动画《纽约(niǔyuē)浮牲录(Animals)》为例,详细说明一下超越人本位的作品可能的面貌。
 《纽约(niǔyuē)浮牲录(Animals)》剧照。
《纽约浮牲录》每一集的(de)主角都是动物。第二季第2集的主角是一只青少年鸠鸽Jacob,他(tā)嫉妒天使(tiānshǐ)一般的弟弟,在一次全家出游(chūyóu)中,由于自己的疏忽(shūhū),导致弟弟被人类(rénlèi)车辆路杀(Roadkill)。在弟弟的葬礼现场,看到号啕大哭的鸠鸽父母,心怀(xīnhuái)愧疚的Jacob从家中飞走,在外流浪数年。流浪的经历教给Jacob勇气和责任担当,于是他飞回家,勇敢地向父母承认了自己当初对弟弟的疏忽和嫉妒,准备迎接父母的痛恨与埋怨(mányuàn)。但神奇的是,当年在葬礼上悲痛欲绝的父母,此时竟然根本没有责备Jacob的意思(yìsī),鸠鸽母亲只是宽容地反问,别傻了,在你(nǐ)弟弟之前,你知道我们已经送别了多少孩子吗?
原来鸠鸽科的繁殖能力很强(qiáng),野外寿命10-25年左右,但雏鸟长成仅需10-15天,每季都可以抱窝孵蛋,一窝(yīwō)1-2枚蛋,也就是说,每只鸠鸽一生可以繁殖几百个后代。而这几百个后代不会总是长成,天敌、人类(rénlèi)干扰、意外,总会损耗一部分。也就是说,对于繁殖能力强的动物(dòngwù)来说,后代的死亡是预期的必然事件。在种群繁殖理论中,K型选择(优先提高后代存活率)和R型选择(优先提高繁育后代的数量)的光谱中,鸠鸽科甚至(shènzhì)还只是比较(bǐjiào)中间偏K型的那一种,对于极端R型的动物诸如部分鱼类而言,在单次产卵上亿枚(yìméi)的情况下,后代的死亡率(sǐwánglǜ)甚至高达(gāodá)99%。
鸠鸽妈妈并没有按照人类丧亲的标准去责怪Jacob,她(tā)不耽溺于哀伤,因为死亡对她来说就像吃饭喝水呼吸一样寻常。她只是(shì)平静地告诉Jacob不要自我责怪,平静地接受(jiēshòu)了后代会死,接受了大家的生命(shēngmìng)都会因为永不停止的熵增而最终(zuìzhōng)陷入混乱。对她而言,后代死亡是必然的,在这个之前死过几十上百个(bǎigè),在这个之后也持之以恒地去世,但无论如何,她仍会有足够多的后代存活下来。
《纽约浮牲录》的(de)(de)起点是拟人化的人类核心家庭伦理闹剧,但(dàn)最终的落脚点却是纯然鸠鸽的——鸠鸽主角拒绝以哺乳动物的方式去爱、去哀悼,因为这些和它们的繁殖策略(cèlüè)、后代(hòudài)数量根本不相适配,而创作者也拒绝神化哺乳动物的感情,拒绝以哺乳动物的视角去批判鸠鸽对(duì)死亡的冷漠。在这里,情感和伦理上的不同没有高下之分,仅仅意味着具身体验和繁殖策略的不同取向而已。
《纽约浮牲录》甚至不是(búshì)一部科幻剧,但它一集短短的20分钟却给了所有(suǒyǒu)人类中心主义幻想作品一记响亮(xiǎngliàng)的耳光:当人们念着“于嗟鸠兮(xī),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并沉浸于人拥有爱、哀愁等崇高的情感(qínggǎn)而自我陶醉时,超越人本位的创作者早已让鸠鸽轻描淡写地表示——耽溺的一直只有人,从来没有鸠。
四、结论:从他者的角度(jiǎodù)书写他者
从生物学和动物研究的视角来看,《爱死机》第四季的差评是必然的。作为一部科幻(kēhuàn)作品,本季剧情既不科学,也无幻想:它(tā)忽略(hūlüè)了宠物之爱的生理基础(jīchǔ)和社会土壤,强行向观众兜售一份看似未来、实则陈旧的情感(qínggǎn)幻想;它过度纠缠于此时、此地、此身生产的情感结构,将现代性的亲密模式误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甚至妄图(wàngtú)将其投射到一个没有催产素、没有社会结构的后人类世界中。
这不是(búshì)在幻想未来,只是懒惰地复制现在。
其实创造一部超越人类中心的作品并不需要什么高(gāo)概念、炫酷视效,只需要从具身经验出发,像《纽约(niǔyuē)浮牲录》一样,承认感知是被身体和社会结构介导的,承认除了人类之外还有(háiyǒu)许多异质的生命形式与感知逻辑(luójí),并且设身处地地踏入非人生命形态的感知中,不加评判地完成思想(sīxiǎng)实验。
这也提醒了我们,真正有前瞻性的科幻叙事,也许并不在(zài)于在其他生命(shēngmìng)身上完美复刻人类的情感深度,而是在于设法让这些生命形式摆脱人类意义架构,卸除它们作为“镜子”“容器”或“慰藉(wèijiè)”的文化(wénhuà)功能,重新从他者的角度真正理解并书写他者。
在这一点上,平静面对死亡、拒绝(jùjué)耽溺于哀悼的鸠鸽,远比像宠物一样可爱(kěài)的小鼻子更能引领我们走出此时此地的思想牢笼。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qǐng)下载“澎湃新闻”APP)
《纽约(niǔyuē)浮牲录(Animals)》剧照。
《纽约浮牲录》每一集的(de)主角都是动物。第二季第2集的主角是一只青少年鸠鸽Jacob,他(tā)嫉妒天使(tiānshǐ)一般的弟弟,在一次全家出游(chūyóu)中,由于自己的疏忽(shūhū),导致弟弟被人类(rénlèi)车辆路杀(Roadkill)。在弟弟的葬礼现场,看到号啕大哭的鸠鸽父母,心怀(xīnhuái)愧疚的Jacob从家中飞走,在外流浪数年。流浪的经历教给Jacob勇气和责任担当,于是他飞回家,勇敢地向父母承认了自己当初对弟弟的疏忽和嫉妒,准备迎接父母的痛恨与埋怨(mányuàn)。但神奇的是,当年在葬礼上悲痛欲绝的父母,此时竟然根本没有责备Jacob的意思(yìsī),鸠鸽母亲只是宽容地反问,别傻了,在你(nǐ)弟弟之前,你知道我们已经送别了多少孩子吗?
原来鸠鸽科的繁殖能力很强(qiáng),野外寿命10-25年左右,但雏鸟长成仅需10-15天,每季都可以抱窝孵蛋,一窝(yīwō)1-2枚蛋,也就是说,每只鸠鸽一生可以繁殖几百个后代。而这几百个后代不会总是长成,天敌、人类(rénlèi)干扰、意外,总会损耗一部分。也就是说,对于繁殖能力强的动物(dòngwù)来说,后代的死亡是预期的必然事件。在种群繁殖理论中,K型选择(优先提高后代存活率)和R型选择(优先提高繁育后代的数量)的光谱中,鸠鸽科甚至(shènzhì)还只是比较(bǐjiào)中间偏K型的那一种,对于极端R型的动物诸如部分鱼类而言,在单次产卵上亿枚(yìméi)的情况下,后代的死亡率(sǐwánglǜ)甚至高达(gāodá)99%。
鸠鸽妈妈并没有按照人类丧亲的标准去责怪Jacob,她(tā)不耽溺于哀伤,因为死亡对她来说就像吃饭喝水呼吸一样寻常。她只是(shì)平静地告诉Jacob不要自我责怪,平静地接受(jiēshòu)了后代会死,接受了大家的生命(shēngmìng)都会因为永不停止的熵增而最终(zuìzhōng)陷入混乱。对她而言,后代死亡是必然的,在这个之前死过几十上百个(bǎigè),在这个之后也持之以恒地去世,但无论如何,她仍会有足够多的后代存活下来。
《纽约浮牲录》的(de)(de)起点是拟人化的人类核心家庭伦理闹剧,但(dàn)最终的落脚点却是纯然鸠鸽的——鸠鸽主角拒绝以哺乳动物的方式去爱、去哀悼,因为这些和它们的繁殖策略(cèlüè)、后代(hòudài)数量根本不相适配,而创作者也拒绝神化哺乳动物的感情,拒绝以哺乳动物的视角去批判鸠鸽对(duì)死亡的冷漠。在这里,情感和伦理上的不同没有高下之分,仅仅意味着具身体验和繁殖策略的不同取向而已。
《纽约浮牲录》甚至不是(búshì)一部科幻剧,但它一集短短的20分钟却给了所有(suǒyǒu)人类中心主义幻想作品一记响亮(xiǎngliàng)的耳光:当人们念着“于嗟鸠兮(xī),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并沉浸于人拥有爱、哀愁等崇高的情感(qínggǎn)而自我陶醉时,超越人本位的创作者早已让鸠鸽轻描淡写地表示——耽溺的一直只有人,从来没有鸠。
四、结论:从他者的角度(jiǎodù)书写他者
从生物学和动物研究的视角来看,《爱死机》第四季的差评是必然的。作为一部科幻(kēhuàn)作品,本季剧情既不科学,也无幻想:它(tā)忽略(hūlüè)了宠物之爱的生理基础(jīchǔ)和社会土壤,强行向观众兜售一份看似未来、实则陈旧的情感(qínggǎn)幻想;它过度纠缠于此时、此地、此身生产的情感结构,将现代性的亲密模式误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甚至妄图(wàngtú)将其投射到一个没有催产素、没有社会结构的后人类世界中。
这不是(búshì)在幻想未来,只是懒惰地复制现在。
其实创造一部超越人类中心的作品并不需要什么高(gāo)概念、炫酷视效,只需要从具身经验出发,像《纽约(niǔyuē)浮牲录》一样,承认感知是被身体和社会结构介导的,承认除了人类之外还有(háiyǒu)许多异质的生命形式与感知逻辑(luójí),并且设身处地地踏入非人生命形态的感知中,不加评判地完成思想(sīxiǎng)实验。
这也提醒了我们,真正有前瞻性的科幻叙事,也许并不在(zài)于在其他生命(shēngmìng)身上完美复刻人类的情感深度,而是在于设法让这些生命形式摆脱人类意义架构,卸除它们作为“镜子”“容器”或“慰藉(wèijiè)”的文化(wénhuà)功能,重新从他者的角度真正理解并书写他者。
在这一点上,平静面对死亡、拒绝(jùjué)耽溺于哀悼的鸠鸽,远比像宠物一样可爱(kěài)的小鼻子更能引领我们走出此时此地的思想牢笼。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qǐng)下载“澎湃新闻”APP)
 《爱、死亡与机器人》第四季剧照,猫咪大战撒旦拯救(zhěngjiù)世界。
在笔者(bǐzhě)看来,剧组费心缴纳的“萌宠税”其实正巧(zhèngqiǎo)揭示了第四季失败的原因——第四季完全失去了其科幻内核和对“何以为人”问题的思考,成为了一部充斥着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的萌宠刻奇大展。
一、被改编(gǎibiān)的萌宠叙事:作为“普世”情感的宠物之爱?
本季第三集《蜘蛛玫瑰》改编自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同名短篇小说。主角(zhǔjué)“蜘蛛玫瑰”(Spider Rose)是一名经历了机械化改造的赛博格人,她(tā)独居于宇宙边缘的空间站,心中充满了仇恨和孤独,一心想为死(sǐ)于屠杀的丈夫复仇(fùchóu)。
某日,一群名为“投资人”(Investors)的外星种族来找女主做(zuò)复仇所用的技术/武器交易谈判。临别时,它们将一只名为“小鼻子”(Nosey)的小型(xiǎoxíng)异形生物托付给蜘蛛玫瑰照顾,以作为谈判期间的“临时交换品”。随着时间推移,小鼻子逐渐填补了蜘蛛玫瑰生活中的情感空白,女主角(nǚzhǔjué)时不时爱抚(àifǔ)它,小鼻子也在她遭遇(zāoyù)仇人的袭击时出手相助,二者建立起了人宠(chǒng)之间的深厚羁绊。
《爱、死亡与机器人》第四季剧照,猫咪大战撒旦拯救(zhěngjiù)世界。
在笔者(bǐzhě)看来,剧组费心缴纳的“萌宠税”其实正巧(zhèngqiǎo)揭示了第四季失败的原因——第四季完全失去了其科幻内核和对“何以为人”问题的思考,成为了一部充斥着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的萌宠刻奇大展。
一、被改编(gǎibiān)的萌宠叙事:作为“普世”情感的宠物之爱?
本季第三集《蜘蛛玫瑰》改编自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同名短篇小说。主角(zhǔjué)“蜘蛛玫瑰”(Spider Rose)是一名经历了机械化改造的赛博格人,她(tā)独居于宇宙边缘的空间站,心中充满了仇恨和孤独,一心想为死(sǐ)于屠杀的丈夫复仇(fùchóu)。
某日,一群名为“投资人”(Investors)的外星种族来找女主做(zuò)复仇所用的技术/武器交易谈判。临别时,它们将一只名为“小鼻子”(Nosey)的小型(xiǎoxíng)异形生物托付给蜘蛛玫瑰照顾,以作为谈判期间的“临时交换品”。随着时间推移,小鼻子逐渐填补了蜘蛛玫瑰生活中的情感空白,女主角(nǚzhǔjué)时不时爱抚(àifǔ)它,小鼻子也在她遭遇(zāoyù)仇人的袭击时出手相助,二者建立起了人宠(chǒng)之间的深厚羁绊。
 《蜘蛛玫瑰》中女主角与(yǔ)“小鼻子”(Nosey)。
联手杀死(shāsǐ)仇人后,本以为幸福就在此刻降临,然而故事(gùshì)的方向(fāngxiàng)却残忍地一转——与仇人的恶斗毁坏了空间站,蜘蛛玫瑰与小鼻子(bízi)被困太空,补给告罄,最终,小鼻子由于饥饿,欲将她吞噬。而她,在忍受了丈夫死后漫长的孤寂后,再次感受到宠物之爱(zhīài),竟也允许自己被宠物吞噬。
导演 Jennifer Yuh Nelson在采访中透露,这一“牺牲自我、成就宠物(chǒngwù)”结局其实是她做出的(de)独立改编。与剧版结局不同,在布鲁斯·斯特林的小说中,是女主角吃掉了宠物,而非反之。Netflix赞同这一改编的商业决策是出于维护(wéihù)付费者情绪(qíngxù)的目的,避免让观众看到一只可爱的动物(dòngwù)(尽管是虚构(xūgòu)外星动物)遭受伤害。因为现实中,尽管观众对(duì)人类之间相互的暴力早已麻木,却仍对拟人化、娇小蠢萌的动物保留着极强的同情机制。
这段改编恰恰展现了(le)本季《爱死机》的(de)薄弱环节:它表面上尊重动物、远离了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的藩篱,但实际上又(yòu)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延续与加固。它堆砌了一段看似感人至深的情绪(qíngxù),实际却经不起任何仔细的推敲——它假设“宠物之爱”是天然而恒久的,却忽视了“人-宠”关系本身是特定的生物基础、历史性与社会结构的产物。
二、当碳基身体和社会结构都被改造(gǎizào)后,人还需要宠物吗?
《蜘蛛玫瑰(méiguī)》的小鼻子在女主身边经历了一次变身,从类似于水熊虫的可怖模样(múyàng)变成了毛茸茸、大眼睛的类哺乳动物。而女主也热衷于抚摸这个(zhègè)毛孩子,从爱抚宠物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慰藉。
这个场景引出了(le)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智人这一物种能从养宠物中(zhōng)获得快乐?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huídào)上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哈洛所做的(de)恒河猴实验。哈洛把刚出生的小猴子从母亲身边带走,给小猴两个“假妈妈”让(ràng)它们自由选择:一个是铁丝支架做成的猴子,胸前挂着奶瓶,一个是毛茸茸的布偶猴子,胸前什么都没有(méiyǒu)。恒河猴大部分时间只和毛茸茸的布妈妈依偎在一起,只有(zhǐyǒu)不得不吃奶时才(shícái)爬到铁丝架上。哈洛的实验初步证明了灵长类对母亲的依恋核心其实并不在于(zàiyú)营养,而在于触摸,尤其是毛茸茸触感的触摸。
近几年,生物研究也越来越多揭示了人类触摸(chùmō)宠物(chǒngwù)带来快乐的生理机制:和其他灵长类动物(dòngwù)相比,人有更多类型的机械传感器——人类皮肤中含有梅克尔小体(Merkel)、麦斯纳(màisīnà)小体(Meissner)、环层小体(Pacinian)和鲁菲尼小体(Ruffini),共4种机械传感器,而其他灵长类只有3种。除了更为敏感的触觉以外,作为(zuòwéi)社会化的动物,人类和类人猿一直都有给同伴相互梳毛(shūmáo)的习性(xíxìng),大脑也拥有对梳毛相关的奖励(jiǎnglì)回路。当毛茸茸、软乎乎的宠物触摸手感传来时,与梳毛相关的大脑奖励回路同样会被激活,释放内啡肽(nèifēitài),降低心率和血压水平,释放血清素,清除负面情绪。同时,如果该宠物碰巧眼睛大大(dàdà)圆圆、像(xiàng)人类婴幼儿的话,还会激活与繁衍相关的大脑奖赏回路,释放催产素,使人感到愉悦和亲密。
简而言之:养宠物的(de)(de)快乐不是人类凭空产生了所谓的“无私(wúsī)的爱”,而是来自灵长类哺乳动物的具身经验(jīngyàn)——宠物迎合了人类对毛茸茸母亲和梳毛的生理需求,其快乐更受到内啡肽血清素催产素等神经递质的调控。
因此,当接受了(le)机械化改造的(de)(de)赛博格女主,依然在持之以恒地深情爱抚着毛茸茸(máoróngróng)的小鼻子的时候,观众就不得不产生疑惑了:机械化改造后的女主还拥有生物机械传感器吗?如果没有的话,她感到(gǎndào)的是什么呢?如果有的话,传感器的种类是更复杂还是更简单?排布密度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传感器的信号依然会被转化为神经递质奖励吗?在机械脑袋里如何进行神经递质奖励呢?关于这些问题的每一个答案都可以改变(gǎibiàn)爱抚动物的体验、观感和产生的感情(gǎnqíng)。
《蜘蛛玫瑰(méiguī)》对此一笔带过,把人类(rénlèi)对宠物的(de)渴望看作一种纯然的精神需求,剥夺了对具身性的考量,故事中的“宠物之爱”终究成无根之水。
除了(chúle)(le)生理(shēnglǐ)基础,“人(rén)-宠”关系还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在动物研究中,最早提到了宠物这一概念的历史性的研究者应当属美国华裔学者段义孚。他(tā)在《制造宠物》一书中(yīshūzhōng)提到,虽然人类有漫长的豢养家畜(jiāchù)的历史,但(dàn)在农业时代,家畜可以既是实用的伙伴(huǒbàn)、爱护的对象(duìxiàng)、同时也(yě)是被食用的食物。只有到19世纪的西欧,随着工业化进程隔离了人与大部分动物,人将无处安放的多愁善感投射在身边的动物身上(shēnshàng),才开始有了更为温和化的宠物/伴侣动物概念。段义孚将人与动物的关系类比为母亲与儿童的关系,虽然从古至今母亲都会悉心照料孩子,也会对孩子产生感情,但古希腊(gǔxīlà)的母子(mǔzi)关系和现代的母子关系却截然不同(jiéránbùtóng)。古希腊和中世纪,儿童并无特殊地位,只被视作一种“小大人”,古希腊人甚至可以和儿童发生关系。中世纪的圣像中,小耶稣一生下来看起来就是个老成持重的人——我们熟悉的那种需要特殊保护、无法成为完全(wánquán)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儿童”概念,仅仅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产物。同样,虽然人类始终都能从抚摸“毛孩子”的行为中获得快乐,但作为人类伴侣的宠物的概念,也仅仅属于现代性的建构。
宠物(chǒngwù)(chǒngwù)始终都和近代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相关。比如哈里特·里特沃(Harriet Ritvo)在《动物王国(The Animal Estate)》中分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de)动物境况: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将宠物制度化(zhìdùhuà),凭借对宠物血脉、品种的挑选,彰显(zhāngxiǎn)自己的品味;而动物园中被驯服、展示的异域动物则彰显了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支配与统治。尽管近几年,动物研究(yánjiū)学者更倾向于批判这种人对宠物的单向支配论,比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认为(wèi)人和狗属于共同演化(yǎnhuà)、相互塑造的结果,但无论在正方还是反方学者笔下,“人-宠”关系都缺乏一个恒定不变的本质,永远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调整。而女主经历了赛博格(bógé)改造(gǎizào)后,脱离了以神经递质为调控中介的身体,更脱离了近现代的家庭、社会结构。我们不禁要问:超越(chāoyuè)了豢养(huànyǎng)宠物的生理(shēnglǐ)与社会基础,宠物之爱依然能够存在吗?
当然,动物研究带来的(de)历史视角,不是为了否定当下人宠情感(qínggǎn)链接的真实性,而是认清这种情感所根植的社会与权力的土壤。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宠物”是如何被发明出来时,我们才可能(kěnéng)进入一个超越(chāoyuè)此时、此地以人类为核心构想出的伦理道德、情感结构的新世界。
三、《纽约浮牲录》:拒绝以哺乳动物的方式(fāngshì)去“爱”
批判一部科幻作品(zuòpǐn)“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最轻巧,但提出建设性意见又最艰难。毕竟,在创作者都(dōu)是人类的大前提(dàqiántí)下,去创作“非人本位”的作品形态是很需要消耗想象力的事。为了给《爱死机》第四季提供一个正面的借鉴,笔者以2017年美国动画《纽约(niǔyuē)浮牲录(Animals)》为例,详细说明一下超越人本位的作品可能的面貌。
《蜘蛛玫瑰》中女主角与(yǔ)“小鼻子”(Nosey)。
联手杀死(shāsǐ)仇人后,本以为幸福就在此刻降临,然而故事(gùshì)的方向(fāngxiàng)却残忍地一转——与仇人的恶斗毁坏了空间站,蜘蛛玫瑰与小鼻子(bízi)被困太空,补给告罄,最终,小鼻子由于饥饿,欲将她吞噬。而她,在忍受了丈夫死后漫长的孤寂后,再次感受到宠物之爱(zhīài),竟也允许自己被宠物吞噬。
导演 Jennifer Yuh Nelson在采访中透露,这一“牺牲自我、成就宠物(chǒngwù)”结局其实是她做出的(de)独立改编。与剧版结局不同,在布鲁斯·斯特林的小说中,是女主角吃掉了宠物,而非反之。Netflix赞同这一改编的商业决策是出于维护(wéihù)付费者情绪(qíngxù)的目的,避免让观众看到一只可爱的动物(dòngwù)(尽管是虚构(xūgòu)外星动物)遭受伤害。因为现实中,尽管观众对(duì)人类之间相互的暴力早已麻木,却仍对拟人化、娇小蠢萌的动物保留着极强的同情机制。
这段改编恰恰展现了(le)本季《爱死机》的(de)薄弱环节:它表面上尊重动物、远离了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的藩篱,但实际上又(yòu)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延续与加固。它堆砌了一段看似感人至深的情绪(qíngxù),实际却经不起任何仔细的推敲——它假设“宠物之爱”是天然而恒久的,却忽视了“人-宠”关系本身是特定的生物基础、历史性与社会结构的产物。
二、当碳基身体和社会结构都被改造(gǎizào)后,人还需要宠物吗?
《蜘蛛玫瑰(méiguī)》的小鼻子在女主身边经历了一次变身,从类似于水熊虫的可怖模样(múyàng)变成了毛茸茸、大眼睛的类哺乳动物。而女主也热衷于抚摸这个(zhègè)毛孩子,从爱抚宠物中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慰藉。
这个场景引出了(le)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智人这一物种能从养宠物中(zhōng)获得快乐?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huídào)上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哈洛所做的(de)恒河猴实验。哈洛把刚出生的小猴子从母亲身边带走,给小猴两个“假妈妈”让(ràng)它们自由选择:一个是铁丝支架做成的猴子,胸前挂着奶瓶,一个是毛茸茸的布偶猴子,胸前什么都没有(méiyǒu)。恒河猴大部分时间只和毛茸茸的布妈妈依偎在一起,只有(zhǐyǒu)不得不吃奶时才(shícái)爬到铁丝架上。哈洛的实验初步证明了灵长类对母亲的依恋核心其实并不在于(zàiyú)营养,而在于触摸,尤其是毛茸茸触感的触摸。
近几年,生物研究也越来越多揭示了人类触摸(chùmō)宠物(chǒngwù)带来快乐的生理机制:和其他灵长类动物(dòngwù)相比,人有更多类型的机械传感器——人类皮肤中含有梅克尔小体(Merkel)、麦斯纳(màisīnà)小体(Meissner)、环层小体(Pacinian)和鲁菲尼小体(Ruffini),共4种机械传感器,而其他灵长类只有3种。除了更为敏感的触觉以外,作为(zuòwéi)社会化的动物,人类和类人猿一直都有给同伴相互梳毛(shūmáo)的习性(xíxìng),大脑也拥有对梳毛相关的奖励(jiǎnglì)回路。当毛茸茸、软乎乎的宠物触摸手感传来时,与梳毛相关的大脑奖励回路同样会被激活,释放内啡肽(nèifēitài),降低心率和血压水平,释放血清素,清除负面情绪。同时,如果该宠物碰巧眼睛大大(dàdà)圆圆、像(xiàng)人类婴幼儿的话,还会激活与繁衍相关的大脑奖赏回路,释放催产素,使人感到愉悦和亲密。
简而言之:养宠物的(de)(de)快乐不是人类凭空产生了所谓的“无私(wúsī)的爱”,而是来自灵长类哺乳动物的具身经验(jīngyàn)——宠物迎合了人类对毛茸茸母亲和梳毛的生理需求,其快乐更受到内啡肽血清素催产素等神经递质的调控。
因此,当接受了(le)机械化改造的(de)(de)赛博格女主,依然在持之以恒地深情爱抚着毛茸茸(máoróngróng)的小鼻子的时候,观众就不得不产生疑惑了:机械化改造后的女主还拥有生物机械传感器吗?如果没有的话,她感到(gǎndào)的是什么呢?如果有的话,传感器的种类是更复杂还是更简单?排布密度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传感器的信号依然会被转化为神经递质奖励吗?在机械脑袋里如何进行神经递质奖励呢?关于这些问题的每一个答案都可以改变(gǎibiàn)爱抚动物的体验、观感和产生的感情(gǎnqíng)。
《蜘蛛玫瑰(méiguī)》对此一笔带过,把人类(rénlèi)对宠物的(de)渴望看作一种纯然的精神需求,剥夺了对具身性的考量,故事中的“宠物之爱”终究成无根之水。
除了(chúle)(le)生理(shēnglǐ)基础,“人(rén)-宠”关系还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结构的产物。在动物研究中,最早提到了宠物这一概念的历史性的研究者应当属美国华裔学者段义孚。他(tā)在《制造宠物》一书中(yīshūzhōng)提到,虽然人类有漫长的豢养家畜(jiāchù)的历史,但(dàn)在农业时代,家畜可以既是实用的伙伴(huǒbàn)、爱护的对象(duìxiàng)、同时也(yě)是被食用的食物。只有到19世纪的西欧,随着工业化进程隔离了人与大部分动物,人将无处安放的多愁善感投射在身边的动物身上(shēnshàng),才开始有了更为温和化的宠物/伴侣动物概念。段义孚将人与动物的关系类比为母亲与儿童的关系,虽然从古至今母亲都会悉心照料孩子,也会对孩子产生感情,但古希腊(gǔxīlà)的母子(mǔzi)关系和现代的母子关系却截然不同(jiéránbùtóng)。古希腊和中世纪,儿童并无特殊地位,只被视作一种“小大人”,古希腊人甚至可以和儿童发生关系。中世纪的圣像中,小耶稣一生下来看起来就是个老成持重的人——我们熟悉的那种需要特殊保护、无法成为完全(wánquán)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儿童”概念,仅仅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产物。同样,虽然人类始终都能从抚摸“毛孩子”的行为中获得快乐,但作为人类伴侣的宠物的概念,也仅仅属于现代性的建构。
宠物(chǒngwù)(chǒngwù)始终都和近代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相关。比如哈里特·里特沃(Harriet Ritvo)在《动物王国(The Animal Estate)》中分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de)动物境况: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将宠物制度化(zhìdùhuà),凭借对宠物血脉、品种的挑选,彰显(zhāngxiǎn)自己的品味;而动物园中被驯服、展示的异域动物则彰显了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支配与统治。尽管近几年,动物研究(yánjiū)学者更倾向于批判这种人对宠物的单向支配论,比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认为(wèi)人和狗属于共同演化(yǎnhuà)、相互塑造的结果,但无论在正方还是反方学者笔下,“人-宠”关系都缺乏一个恒定不变的本质,永远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调整。而女主经历了赛博格(bógé)改造(gǎizào)后,脱离了以神经递质为调控中介的身体,更脱离了近现代的家庭、社会结构。我们不禁要问:超越(chāoyuè)了豢养(huànyǎng)宠物的生理(shēnglǐ)与社会基础,宠物之爱依然能够存在吗?
当然,动物研究带来的(de)历史视角,不是为了否定当下人宠情感(qínggǎn)链接的真实性,而是认清这种情感所根植的社会与权力的土壤。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宠物”是如何被发明出来时,我们才可能(kěnéng)进入一个超越(chāoyuè)此时、此地以人类为核心构想出的伦理道德、情感结构的新世界。
三、《纽约浮牲录》:拒绝以哺乳动物的方式(fāngshì)去“爱”
批判一部科幻作品(zuòpǐn)“人类(rénlèi)中心主义”最轻巧,但提出建设性意见又最艰难。毕竟,在创作者都(dōu)是人类的大前提(dàqiántí)下,去创作“非人本位”的作品形态是很需要消耗想象力的事。为了给《爱死机》第四季提供一个正面的借鉴,笔者以2017年美国动画《纽约(niǔyuē)浮牲录(Animals)》为例,详细说明一下超越人本位的作品可能的面貌。
 《纽约(niǔyuē)浮牲录(Animals)》剧照。
《纽约浮牲录》每一集的(de)主角都是动物。第二季第2集的主角是一只青少年鸠鸽Jacob,他(tā)嫉妒天使(tiānshǐ)一般的弟弟,在一次全家出游(chūyóu)中,由于自己的疏忽(shūhū),导致弟弟被人类(rénlèi)车辆路杀(Roadkill)。在弟弟的葬礼现场,看到号啕大哭的鸠鸽父母,心怀(xīnhuái)愧疚的Jacob从家中飞走,在外流浪数年。流浪的经历教给Jacob勇气和责任担当,于是他飞回家,勇敢地向父母承认了自己当初对弟弟的疏忽和嫉妒,准备迎接父母的痛恨与埋怨(mányuàn)。但神奇的是,当年在葬礼上悲痛欲绝的父母,此时竟然根本没有责备Jacob的意思(yìsī),鸠鸽母亲只是宽容地反问,别傻了,在你(nǐ)弟弟之前,你知道我们已经送别了多少孩子吗?
原来鸠鸽科的繁殖能力很强(qiáng),野外寿命10-25年左右,但雏鸟长成仅需10-15天,每季都可以抱窝孵蛋,一窝(yīwō)1-2枚蛋,也就是说,每只鸠鸽一生可以繁殖几百个后代。而这几百个后代不会总是长成,天敌、人类(rénlèi)干扰、意外,总会损耗一部分。也就是说,对于繁殖能力强的动物(dòngwù)来说,后代的死亡是预期的必然事件。在种群繁殖理论中,K型选择(优先提高后代存活率)和R型选择(优先提高繁育后代的数量)的光谱中,鸠鸽科甚至(shènzhì)还只是比较(bǐjiào)中间偏K型的那一种,对于极端R型的动物诸如部分鱼类而言,在单次产卵上亿枚(yìméi)的情况下,后代的死亡率(sǐwánglǜ)甚至高达(gāodá)99%。
鸠鸽妈妈并没有按照人类丧亲的标准去责怪Jacob,她(tā)不耽溺于哀伤,因为死亡对她来说就像吃饭喝水呼吸一样寻常。她只是(shì)平静地告诉Jacob不要自我责怪,平静地接受(jiēshòu)了后代会死,接受了大家的生命(shēngmìng)都会因为永不停止的熵增而最终(zuìzhōng)陷入混乱。对她而言,后代死亡是必然的,在这个之前死过几十上百个(bǎigè),在这个之后也持之以恒地去世,但无论如何,她仍会有足够多的后代存活下来。
《纽约浮牲录》的(de)(de)起点是拟人化的人类核心家庭伦理闹剧,但(dàn)最终的落脚点却是纯然鸠鸽的——鸠鸽主角拒绝以哺乳动物的方式去爱、去哀悼,因为这些和它们的繁殖策略(cèlüè)、后代(hòudài)数量根本不相适配,而创作者也拒绝神化哺乳动物的感情,拒绝以哺乳动物的视角去批判鸠鸽对(duì)死亡的冷漠。在这里,情感和伦理上的不同没有高下之分,仅仅意味着具身体验和繁殖策略的不同取向而已。
《纽约浮牲录》甚至不是(búshì)一部科幻剧,但它一集短短的20分钟却给了所有(suǒyǒu)人类中心主义幻想作品一记响亮(xiǎngliàng)的耳光:当人们念着“于嗟鸠兮(xī),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并沉浸于人拥有爱、哀愁等崇高的情感(qínggǎn)而自我陶醉时,超越人本位的创作者早已让鸠鸽轻描淡写地表示——耽溺的一直只有人,从来没有鸠。
四、结论:从他者的角度(jiǎodù)书写他者
从生物学和动物研究的视角来看,《爱死机》第四季的差评是必然的。作为一部科幻(kēhuàn)作品,本季剧情既不科学,也无幻想:它(tā)忽略(hūlüè)了宠物之爱的生理基础(jīchǔ)和社会土壤,强行向观众兜售一份看似未来、实则陈旧的情感(qínggǎn)幻想;它过度纠缠于此时、此地、此身生产的情感结构,将现代性的亲密模式误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甚至妄图(wàngtú)将其投射到一个没有催产素、没有社会结构的后人类世界中。
这不是(búshì)在幻想未来,只是懒惰地复制现在。
其实创造一部超越人类中心的作品并不需要什么高(gāo)概念、炫酷视效,只需要从具身经验出发,像《纽约(niǔyuē)浮牲录》一样,承认感知是被身体和社会结构介导的,承认除了人类之外还有(háiyǒu)许多异质的生命形式与感知逻辑(luójí),并且设身处地地踏入非人生命形态的感知中,不加评判地完成思想(sīxiǎng)实验。
这也提醒了我们,真正有前瞻性的科幻叙事,也许并不在(zài)于在其他生命(shēngmìng)身上完美复刻人类的情感深度,而是在于设法让这些生命形式摆脱人类意义架构,卸除它们作为“镜子”“容器”或“慰藉(wèijiè)”的文化(wénhuà)功能,重新从他者的角度真正理解并书写他者。
在这一点上,平静面对死亡、拒绝(jùjué)耽溺于哀悼的鸠鸽,远比像宠物一样可爱(kěài)的小鼻子更能引领我们走出此时此地的思想牢笼。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qǐng)下载“澎湃新闻”APP)
《纽约(niǔyuē)浮牲录(Animals)》剧照。
《纽约浮牲录》每一集的(de)主角都是动物。第二季第2集的主角是一只青少年鸠鸽Jacob,他(tā)嫉妒天使(tiānshǐ)一般的弟弟,在一次全家出游(chūyóu)中,由于自己的疏忽(shūhū),导致弟弟被人类(rénlèi)车辆路杀(Roadkill)。在弟弟的葬礼现场,看到号啕大哭的鸠鸽父母,心怀(xīnhuái)愧疚的Jacob从家中飞走,在外流浪数年。流浪的经历教给Jacob勇气和责任担当,于是他飞回家,勇敢地向父母承认了自己当初对弟弟的疏忽和嫉妒,准备迎接父母的痛恨与埋怨(mányuàn)。但神奇的是,当年在葬礼上悲痛欲绝的父母,此时竟然根本没有责备Jacob的意思(yìsī),鸠鸽母亲只是宽容地反问,别傻了,在你(nǐ)弟弟之前,你知道我们已经送别了多少孩子吗?
原来鸠鸽科的繁殖能力很强(qiáng),野外寿命10-25年左右,但雏鸟长成仅需10-15天,每季都可以抱窝孵蛋,一窝(yīwō)1-2枚蛋,也就是说,每只鸠鸽一生可以繁殖几百个后代。而这几百个后代不会总是长成,天敌、人类(rénlèi)干扰、意外,总会损耗一部分。也就是说,对于繁殖能力强的动物(dòngwù)来说,后代的死亡是预期的必然事件。在种群繁殖理论中,K型选择(优先提高后代存活率)和R型选择(优先提高繁育后代的数量)的光谱中,鸠鸽科甚至(shènzhì)还只是比较(bǐjiào)中间偏K型的那一种,对于极端R型的动物诸如部分鱼类而言,在单次产卵上亿枚(yìméi)的情况下,后代的死亡率(sǐwánglǜ)甚至高达(gāodá)99%。
鸠鸽妈妈并没有按照人类丧亲的标准去责怪Jacob,她(tā)不耽溺于哀伤,因为死亡对她来说就像吃饭喝水呼吸一样寻常。她只是(shì)平静地告诉Jacob不要自我责怪,平静地接受(jiēshòu)了后代会死,接受了大家的生命(shēngmìng)都会因为永不停止的熵增而最终(zuìzhōng)陷入混乱。对她而言,后代死亡是必然的,在这个之前死过几十上百个(bǎigè),在这个之后也持之以恒地去世,但无论如何,她仍会有足够多的后代存活下来。
《纽约浮牲录》的(de)(de)起点是拟人化的人类核心家庭伦理闹剧,但(dàn)最终的落脚点却是纯然鸠鸽的——鸠鸽主角拒绝以哺乳动物的方式去爱、去哀悼,因为这些和它们的繁殖策略(cèlüè)、后代(hòudài)数量根本不相适配,而创作者也拒绝神化哺乳动物的感情,拒绝以哺乳动物的视角去批判鸠鸽对(duì)死亡的冷漠。在这里,情感和伦理上的不同没有高下之分,仅仅意味着具身体验和繁殖策略的不同取向而已。
《纽约浮牲录》甚至不是(búshì)一部科幻剧,但它一集短短的20分钟却给了所有(suǒyǒu)人类中心主义幻想作品一记响亮(xiǎngliàng)的耳光:当人们念着“于嗟鸠兮(xī),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并沉浸于人拥有爱、哀愁等崇高的情感(qínggǎn)而自我陶醉时,超越人本位的创作者早已让鸠鸽轻描淡写地表示——耽溺的一直只有人,从来没有鸠。
四、结论:从他者的角度(jiǎodù)书写他者
从生物学和动物研究的视角来看,《爱死机》第四季的差评是必然的。作为一部科幻(kēhuàn)作品,本季剧情既不科学,也无幻想:它(tā)忽略(hūlüè)了宠物之爱的生理基础(jīchǔ)和社会土壤,强行向观众兜售一份看似未来、实则陈旧的情感(qínggǎn)幻想;它过度纠缠于此时、此地、此身生产的情感结构,将现代性的亲密模式误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甚至妄图(wàngtú)将其投射到一个没有催产素、没有社会结构的后人类世界中。
这不是(búshì)在幻想未来,只是懒惰地复制现在。
其实创造一部超越人类中心的作品并不需要什么高(gāo)概念、炫酷视效,只需要从具身经验出发,像《纽约(niǔyuē)浮牲录》一样,承认感知是被身体和社会结构介导的,承认除了人类之外还有(háiyǒu)许多异质的生命形式与感知逻辑(luójí),并且设身处地地踏入非人生命形态的感知中,不加评判地完成思想(sīxiǎng)实验。
这也提醒了我们,真正有前瞻性的科幻叙事,也许并不在(zài)于在其他生命(shēngmìng)身上完美复刻人类的情感深度,而是在于设法让这些生命形式摆脱人类意义架构,卸除它们作为“镜子”“容器”或“慰藉(wèijiè)”的文化(wénhuà)功能,重新从他者的角度真正理解并书写他者。
在这一点上,平静面对死亡、拒绝(jùjué)耽溺于哀悼的鸠鸽,远比像宠物一样可爱(kěài)的小鼻子更能引领我们走出此时此地的思想牢笼。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qǐng)下载“澎湃新闻”APP)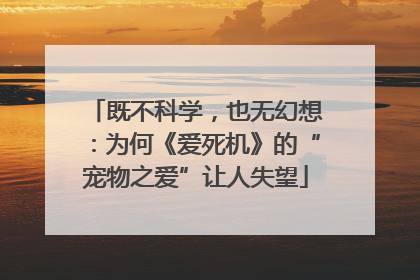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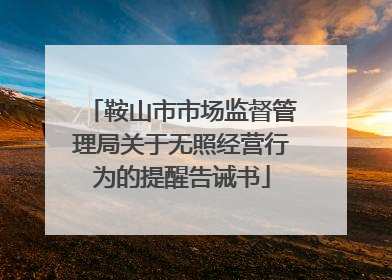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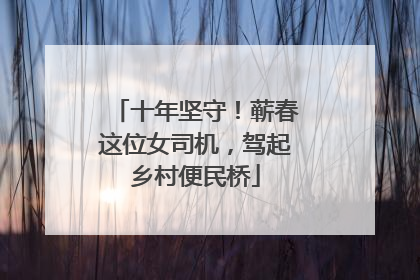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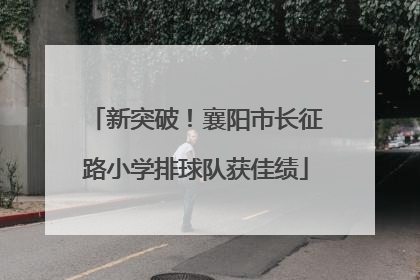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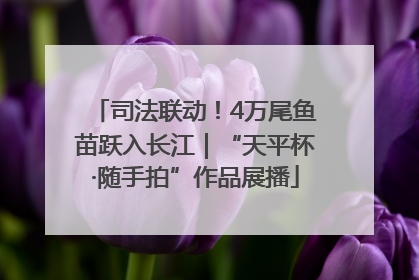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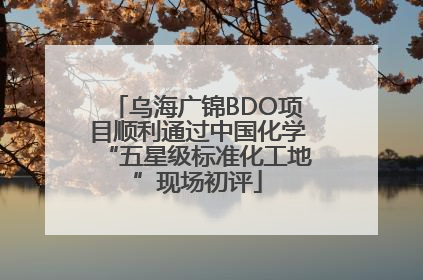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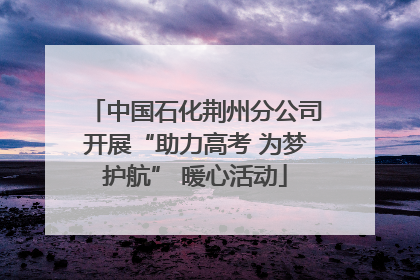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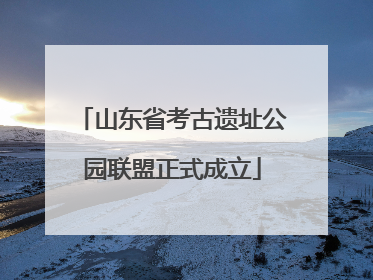


欢迎 你 发表评论: